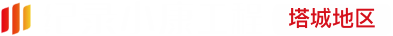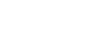从我接受启蒙教育走进校园开始,小学、中学、师范,直到今天我工作的阵地,依然是校园,三十多年来,无论我走到哪里,校园与我息息相关。
七十年代末期,我家住在察汗托海牧场一队,那里家家户户的房屋都是用石滚夯出的土墙。队长利用秋后的空闲,带领全队劳动力,在大队东边一块平阔的土地上,盖了几间土墙屋子,那就是最初的一队小学。学校刚建成,没有桌椅,没有黑板,队上的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。捐木头,打土块。父辈们在教室里比划好,两头砌上土块的台柱,上面搭一块木板,这就是最原始的课桌。七岁那年,爸爸牵着我的手走进了这所小学,走进一年级教室,那教室真小,窗户也真小。仅有的几条长凳上已坐满了学生。往哪儿坐呢?我呆呆地站着,班主任张老师摇完铃走进教室,看看我,又看看教室里的其他同学,对爸爸说:“想想办法吧,总不能让孩子站着上课。”他和爸爸商量了一会儿,两人便忙活开了。他们先在地上量好距离,挖了两个深深的洞,栽进两根半粗的木桩,然后在木桩上钉上一块木板,一条最简易的长凳出现在我面前,就这样,我坐在这长凳上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节课。那节课老师讲的什么我已记不清了,记得最清楚的是老师额前汗湿的头发和那条不能移动的长凳,在这条特殊的长凳上,我一坐就是三年。三年里,因为课桌没有抽屉,妈妈给我缝的布书包在桌下老是被踩脏,妈妈常给我洗书包,也常暗暗叹息:“什么时候,孩子才能坐上有抽屉的课桌呢?”
一九八三年的冬天,我随妈妈辗转回到外婆的家乡,在江苏扬州的一所实验小学读书。在那里,我看到了高大气派的教学楼,坐上了闪闪发亮的电镀椅子,电铃唤我上课,风琴伴我唱歌。种种先进的教学设施让我大开眼界。可在梦中,我依然神往裕民边陲那贫穷的土地,我常想起昔日的小伙伴,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样的校园。
一九九一年的春天,我又回到了新疆,回到了察汗托海牧场中学,这时的校园依然没有围墙,但三间教室已是红砖白墙,光线明亮。桌椅虽然破旧,但已是有抽屉,能移动的正规课桌椅。转眼,秋天来临,由于学校经费紧张,买的煤很少很少。校领导决定全校师生一起上山打柴。山上的灌木丛密密层层,看着不粗的枝条却极有韧性。老师和男生用砍刀砍,女生便用手折,能碰到几棵枯死的树丛,便兴奋地欢呼雀跃。太阳落山了,我们每人背上都背着一大捆树枝,每个人的手上都划出了一道道血痕,火辣辣地疼。夕阳的余辉中,师生背上的柴捆跳跃着、移动着,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,那年冬天,天气格外冷,堆得像小山似的树枝迅速地减少,每天班里分到的一小桶煤和树枝很快化为灰烬,教室里依然冰凉。我常幻想,要是这一堆树枝能变成煤,那该多好!班主任常带着我们在操场上跑步驱寒,鼓励我们好好学习,将来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。
一九九五年九月,我从师范学校毕业,被分配到县第三小学工作。我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学校报到的。走进校门,一队上体育课的学生从我眼前跑过,操场上腾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飞扬。我看到学校的操场四周有三排红砖教室,西北角上有三间破旧的土屋,热心的学生告诉我,那就是老师的办公室,这就是学校最初留给我的印象。一九九九年的暑假,七月流火,学校领导和教职工协商,决定利用假期休息时间,自己动手打制水泥地坪。两千多平方米的水泥地坪,在终日与粉笔书本打交道的老师眼里,真是个巨大的工程。说干就干,顶着骄阳,带着干粮,坐着颠簸不停的小四轮,到东河坝去筛沙子,捡石头,全体教师,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拉回了六百六十多立方的沙石。在这一群老师 ,有的年老体弱;有的家中有病重的老母亲需要照顾;有的身怀六甲,行动不便;有的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孩子。可他们都来了,义无反顾,责无旁贷。叶长华老师,虽说才四十多岁,可身体常年有病,常常听到她因严重咽炎引起的嘶哑的声音,常常看到她在医务室里一边打着点滴,一边批改作业。那年四月,她刚做过胆结石摘除手术,刀口愈合得很慢,医生嘱咐她不能过度劳累。可她硬撑着也来了,一手扶着刀口,一手麻利地捡着石头,豆大的汗珠顺着她清瘦的脸颊往下滚落,大家看着不忍心,都劝她回去休息,别再来了,几个年轻老师主动要求分担她的任务,可第二天一大早,叶老师又来了,身后还跟着刚上初一的儿子,那一刻,我的眼眶发热,很多老师也悄悄背转了身子。
时间过得真快,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二十五年。二十多年来,党和国家的援疆政策,对西部边陲的大力扶持,让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二十多年来,我亲眼目睹了学校的巨大的变化,也亲身体验了创业的艰辛和甘甜。今天,我们的校园里,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,各种功能教室应有尽有,今天的孩子坐在光线明亮的教室里,学习英语,操作计算机; 他们在实验室里观察,在塑胶操场上奔跑。我儿时的梦幻已经成为现实,西部边陲正用最快的步伐赶上时代的潮流。
每当我站在校园里,看学生们认真静心地学习,伫立在街头,看人来人往、日升日落,就能感受到时光缓缓流逝的和谐与安详,心中升腾起对祖国的无限感恩和美好祝福。